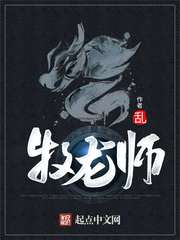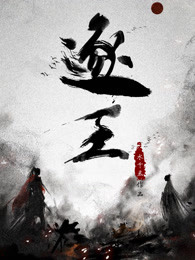114小说网>归处有青山 > 第1740章 岁寒灯暖(第5页)
第1740章 岁寒灯暖(第5页)
夫人轻描淡写地摆手,管家立刻掏钱袋。
柜台另一端,粗布衣裙的少女却反复摩挲着一截藕荷色棉布,小声问:
"能。。。能剪半尺吗?我想给娘亲缝个抹额。。。"
易年绕过布庄,差点踩到蹲在路边玩陀螺的孩童。
那孩子抬头瞪他,手里还攥着根糖葫芦。
不远处,算命摊的幡子在风中翻卷,上面"铁口直断"四个字已经褪色。
穿道袍的瞎子正拉着个商贩打扮的中年人念叨:"。。。流年不利,须请太岁。。。"
"新鲜河鲤!最后一网——"
水产摊前水花四溅,几条青背大鱼在木盆里扑腾。
穿胶皮围裙的鱼贩手起刀落,鱼头整齐斩下,血水溅在雪地上格外刺目。
卖鱼的婆子们七嘴八舌:"给我挑肥的!"
"鳃要鲜红的!"
街心突然爆发喝彩。
原来是卖艺的兄妹开了场,小姑娘踩着高跷翻跟头,红绸裤像两朵跳跃的火苗。
铜钱雨点般落入铜锣,哥哥抱拳作揖:
"谢各位老爷赏!再来个凤凰三点头!"
易年被人流推着向前,不时有小吃摊的热气扑在脸上。
炸鹌鹑的油锅"滋啦"作响,蒸糕的笼屉揭开时白雾弥漫,卖酒酿的摊子前围着几个脸颊通红的老汉。
一切都太鲜活,太热闹,仿佛渭南三州的战火只是说书人嘴里的故事。
直到他看见巷口的粥棚。
青布搭的简易棚子下,几个僧人正在施粥。
队伍排得老长,多是衣衫单薄的外乡人。
有个跛脚老汉捧着碗,蹲在墙角小心地啜饮,胡须上沾着几粒米。
穿官靴的差役路过时,他慌忙把碗藏进怀里,按律法,难民不得在主干道乞食。
"娘,我要那个!"
清脆的童声引得易年回头。锦衣小男孩正指着糖画摊子上的龙凤呈祥,身后奶妈连忙掏荷包。
摊主笑呵呵地舀起一勺糖浆:"小公子属什么?给您画个生肖。。。"
原来,快过年了…
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