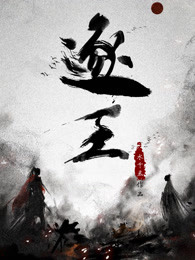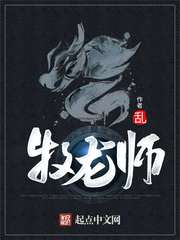114小说网>朕真的不务正业 > 第一千零五十七章 城巴佬就是城巴佬(第3页)
第一千零五十七章 城巴佬就是城巴佬(第3页)
更加明确且具体的定义封建,就是封君和封臣的契约关系。
封君给封臣领地,并且为封臣提供保护;
而封臣需要宣誓效忠,承诺进贡,劳役、兵役、税赋等义务。
封臣在自己的封地享有统治权,西周时诸侯、大夫等等封臣,在他们的封地上,就是实际上的国王。
可自秦以来,郡县帝制,皇帝授官,是完全的上下级的单向隶属关系,官员没有封地,他们在辖区之内,不是为所欲为,严密的监察网,监察着这些地方官员的一举一动。
简而言之,官员手中的权力,来自于组织的授予权限;
而封臣们的权力,来自于分封建国,来源于双向契约。
大明有世袭土官,改土归流,就是在反封建。
这第一个框,就框死了讨论的框架,否定郡县制,等于否定天下为公。
第二个框,则是秦亡于政而非亡于制,秦朝灭亡的原因不在于制度问题,而在于朝堂政斗导致失控,政令出现了问题。
这个框,就是框死了今天的聚谈,不能出现反贼言论。
秦的制度是没问题,要是秦亡于制,那岂不是说,用郡县制的大明,也会和秦朝一样必然灭亡?这就是反贼言论。
“诚如此。”顾宪成认可了聚谈的两个大前提,不法古搞封建,不反对郡县制;不发表任何反贼言论。
焦竑奇怪的看了顾宪成一眼,今天的议题是:寓封建于郡县,这两个大框架顾宪成居然肯同意,那顾宪成还要讲什么?
“秦制,看起来就是郡县制吗?在某看来,绝非如此的简单。”顾宪成端着手,他因为被革除功名的缘故,对每一次的聚谈都很珍惜,为了这天,他做了很多的准备。
“郡县之根本,在于官吏,通过官吏治理四方,来确保朝廷对地方的管理,既然根本在官吏之上,那郡县就有三个基石,其一遴选、其二考核,其三,监察。”
“自始皇帝以来,看起来是儒家当道,但骨还是法骨,对官吏进行遴选、考核、监察,其目的是实现法家梦寐以求的:事在四方,要在中央。”
顾宪成琢磨了这么多年,他逐渐也看明白了一些事儿。
表面上看儒家是显学,独家学问,历朝历代都靠着儒学选官,但仔细一看,其实从来都是法家。
因为几乎所有的制度,都是围绕着对官吏遴选、考核和监察进行,这些制度的目的,都是为了实现,事在四方,要在中央这一政治目标,这是法家的大同世界、理想国、乌托邦。
儒家讲的‘尊尊、亲亲、贤贤’,是政治正确,但不是政治目标,也就是说儒家是实现法家目标的工具。
本小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!
只有搞明白了这个前提,顾宪成接下来的话才容易被理解。
“当下之天下,其实地方仍然处于封建之下。”顾宪成抛出了他的第一个暴论。
此言一出,士人们不断的议论纷纷,这个问题,其实很早就被人注意到了,只不过没人公然讲出来而已。
“买田者多为乡官,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,已十倍于前,父以是传之子,兄以是传之弟,吏胥窟穴其中。”顾宪成压住了现场的议论声,继续陈述自己的观点。
就顾宪成看到的现象,大明的兼并,不仅仅是天灾人祸和乡贤缙绅,更多的是乡官。
乡官这个词,顾宪成也详细解释了,他们在大明朝堂上被叫做吏,尤其是州县衙门的吏员。
地方上的吏员,几乎都是父子相传,他们也在四处买田兼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