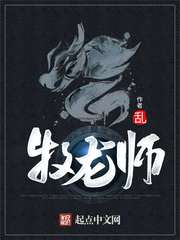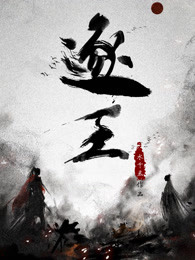114小说网>重生破案:我的眼睛能锁定凶手 > 第776章 消失的公交车(106)(第2页)
第776章 消失的公交车(106)(第2页)
叶默和郑孟俊便已动身,踏上了前往青羊区刑警总队的行程。
长途火车硬邦邦的座椅、空气中混杂着泡面和消毒水的气味,与窗外不断流动的景色,构成了一个移动的、略显沉闷的空间。
郑孟俊坐在叶默对面,身体微微倾向车窗。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
他看着窗外那不断飞速后移的青山绿树、田野村庄,眼神却有些发直,焦点并未真正落在那些景物上。
一种复杂难言的情绪笼罩着他,那不仅仅是不舍,更像是一种从悲壮故事抽离后、回归程式化现实的巨大落差感,以及内心深处对那桩已近乎结案的事,仍残存的一丝难以抚平的褶皱。
沉默了许久,车厢的噪音仿佛成了唯一的背景音。
终于,郑孟俊转过头,目光投向对面始终沉静如水的叶默,声音压得有些低,带着不确定和思索:“叶队,其实…这案子里,是不是还有些…没完全捋顺的疑点?”
闻言,叶默的视线从手中一份泛旧的案卷资料上抬起,但他没有立刻看向郑孟俊,而是将目光先投向了窗外,看了几秒那流逝的风景,仿佛在整理思绪。
沉默了片刻之后,他才缓缓转过头,眼神平静却肯定地开口道:“就算还有疑点,从司法程序和现实角度,也已经没有继续深挖下去的必要了。我可以百分百确定,朱青扎布就是德吉杀的。动机、能力、时间、以及他本人的那本日记,都指向这一点。”
“但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直接指向德吉的物证啊。”郑孟俊身体前倾,手肘撑在窄小的桌板上,语气急切了几分:“现场没有指纹,毛发,仅凭德吉的那个笔记本,在法律上能作为给他定死的铁证吗?我们如何排除他是否在日记里夸大了自己的行为,或者甚至……有没有万分之一的可能,是别人做的,他只是知情甚至顶罪?”
叶默似乎早就料到他会这么问,所以他的回答得条理清晰:“定罪讲求证据链,日记是重要一环,但并非唯一。我如此确定,还因为朱青扎布的死亡方式。那和德吉他们部落里处理牦牛时,为了减少痛苦、追求一刀毙命的传统手法高度吻合。干净利落,精准狠辣。而且,我特意复查过当年的尸检报告和现场照片,并重新询问了德吉的亲友,德吉是个左撇子。”
他停顿了一下,让这个信息沉淀:“而朱青扎布脖颈处的致命伤口,是从正面造成的,利刃切入的角度和深度都显示凶手力道极大且极其熟练,伤口轨迹微微朝右下方倾斜,正好完美地避开了胸骨,一刀捅穿了心脏。这非常符合一个强壮的左撇子凶手的发力习惯。德吉出生在草原,常年骑马摔打,体力充沛,更关键的是,他日常使用藏刀割肉进食,对手中刀的掌控力远超常人。结合他当时复仇的决绝心态,想要杀死朱青扎布,对他而言并非难事。”
郑孟俊消化着这些技术细节,眉头却皱得更紧了:“可是叶队,你刚才…其实也默认了还有疑点这个说法。我心里硌得慌的就是这些地方。我想知道,在你看来,这些没能完全解释通的疑点,具体都包括哪些?”
叶默向后靠向椅背,车厢微微摇晃,他的声音依旧平稳:“首先,是德吉在日记本中的陈述。他说他97年到了甘孜后,问遍了当地人还有桑玛的父母,都没有桑玛的消息。但根据我们后续极其细致的走访调查,桑玛的父母以及她家周边的老邻居、当年的村干部,都非常肯定地表示,从未见过这样一个来自康巴草原、打听桑玛下落的年轻藏族小伙子。如果德吉真的进行了如此大范围的询问,不可能不留下一丝痕迹,更不可能所有人都对他毫无印象。那么,他日记里所说的‘问遍了’,究竟是怎么问的?还是说,他获取信息的渠道,并非如他日记所记的那般直接?”
“然后是第二个疑点!”叶默继续道:交通工具,德吉虽然骑马技术顶尖,但他是否掌握骑摩托车的技能这点存疑,我询问过扎西坎多、拉玛姑妈以及俱乐部里还记得他的老人,所有人的反馈都很一致:没人见过德吉骑摩托车,甚至没人听说他会骑。他出远门要么骑马,要么坐班车。然而,卷宗里记录得很清楚,朱青扎布生前常骑的那辆摩托车,在他死后就离奇消失了,至今未能找到。如果德吉不会骑摩托车,他是如何处置那辆摩托的?如果他需要长途跋涉去挖尸、转移骸骨,没有便捷的交通工具,几乎是不可想象的。”
闻言,郑孟俊沉思了一会,随后提出了不同的见解:“关于摩托车的这个问题,叶队,我有不一样的看法。德吉在日记本里提到,他跟踪了朱青扎布很久,为了最终杀掉朱青扎布,他足足准备、潜伏了好几个月。以他的学习能力和心性,在这段时间里,他完全有时间、也有动机去偷偷学会骑摩托车这门并不算特别复杂的技能。毕竟他是骑马的好手,对平衡感和机械操控有一种天生的领悟力。我认为这并非不可能。反过来想,如果没有摩托车这类交通工具,他后续的一系列操作,比如说杀人后迅速离开现场、更重要的是夜间前往偏僻的贝陀寺挖出桑玛的尸体并将其转移,那么远的路程,还要携带工具和遗骸,没有便捷的交通工具是极为不便的,几乎会增加十倍的风险和难度。从逻辑上,我倾向于他学会了,只是极为隐秘,未被旁人察觉。”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
“你这个观点我也认同,可能性很大。”叶默点了点头:“所以我才说,即便存在这些疑点,从整体证据链和逻辑上看,已经不足以动摇核心结论,也没有投入无限资源去调查下去的必要了。案子,总要有一个了结。”
他话锋微微一转,声音压得更低了些,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个纯粹的推理:“其实,在我个人的推断里,德吉在杀死朱青扎布以及后续处理尸体的过程中,有一个帮手,或许能更完美地解释这些疑点!如有人帮他学会了骑车,有人帮他处理了摩托,甚至有人帮他打听到了我们未能查出的信息。但这……”
他轻轻摇了摇头:“但这仅仅是我基于疑点所做的、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推理。现在,只要法医那边的DNA化验结果出来,确认木盒中的遗骸就是桑玛,那么针对朱青扎布被杀案,证据链就基本完整了。日记提供了动机和自认,DNA证据将两案彻底关联,死亡方式与德吉身份特征吻合。这,就够了。”
郑孟俊的担忧似乎转移了:“就盒子里那些骸骨碎片,经历了这么多年,又是在那种环境下,真的还能够提取到有效的DNA吗?万一降解了呢?”
“成功的概率很高!”叶默的语气十分肯定,显示了他对刑事科学技术的了解:“因为那并不是高温焚化后的骨灰,其中有一些牙齿碎片和密度较高的骨骼碎片保存得相对比较完整,这些都是提取DNA的理想检材。更重要的是,这些遗骸被放置在一个几乎是密封的木盒里,深埋于地下。这种缺氧、避光、恒温低温的环境,极大地减缓了DNA的降解速度。法医那边有信心。”
谈话至此,车厢内再次陷入了沉默。
火车依旧轰隆向前,载着他们和案卷,驶向程序意义上的终点站。
窗外的景色依旧,但两人心中的波澜,却远未平息。